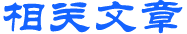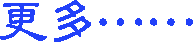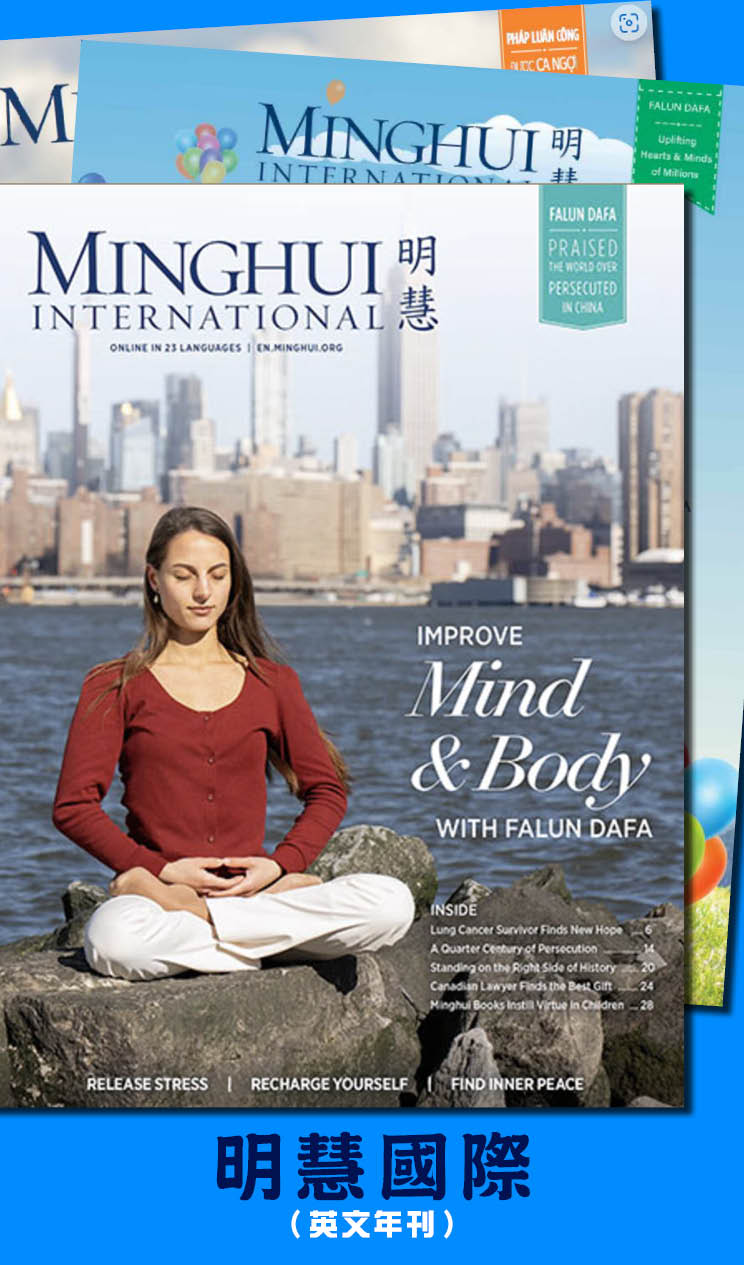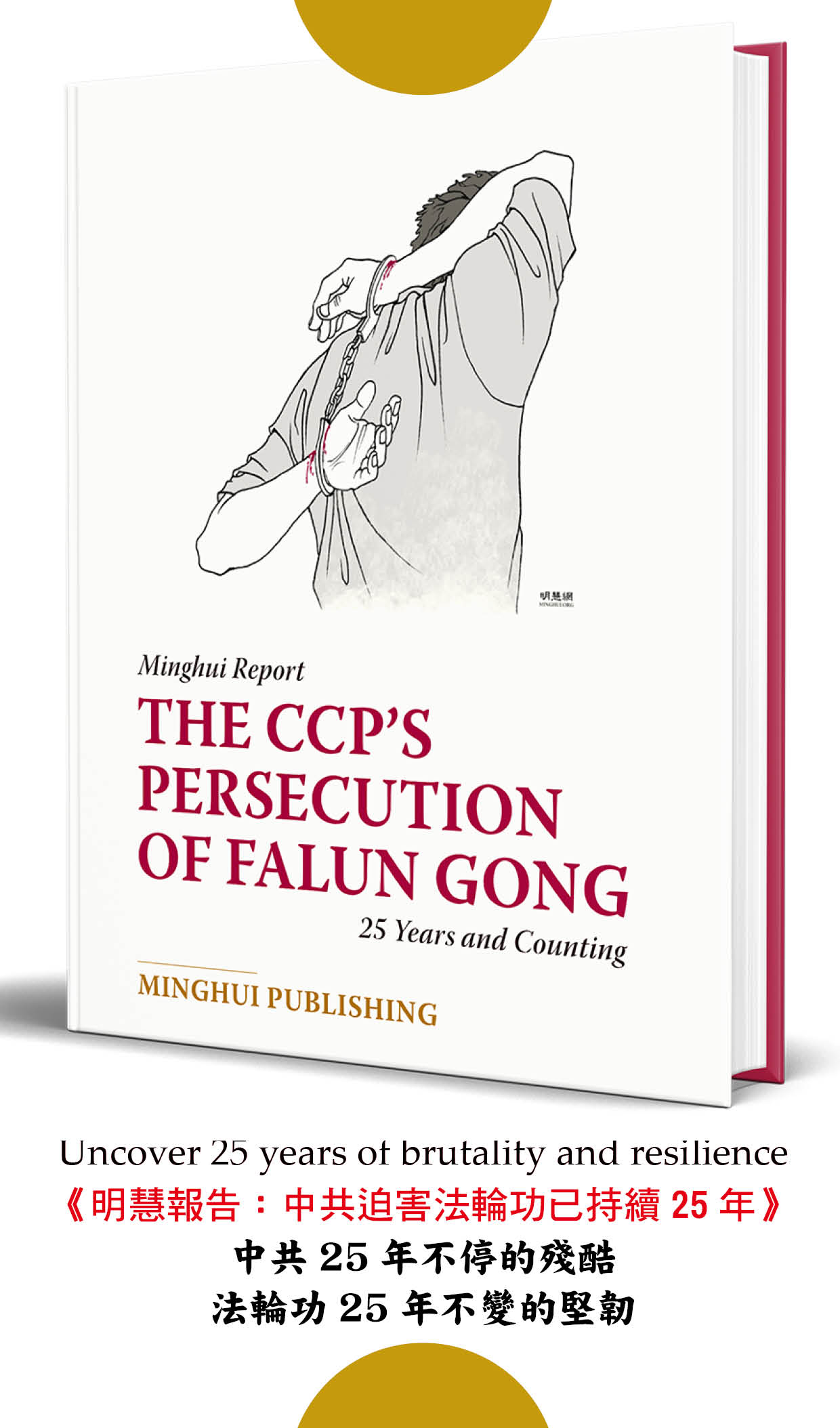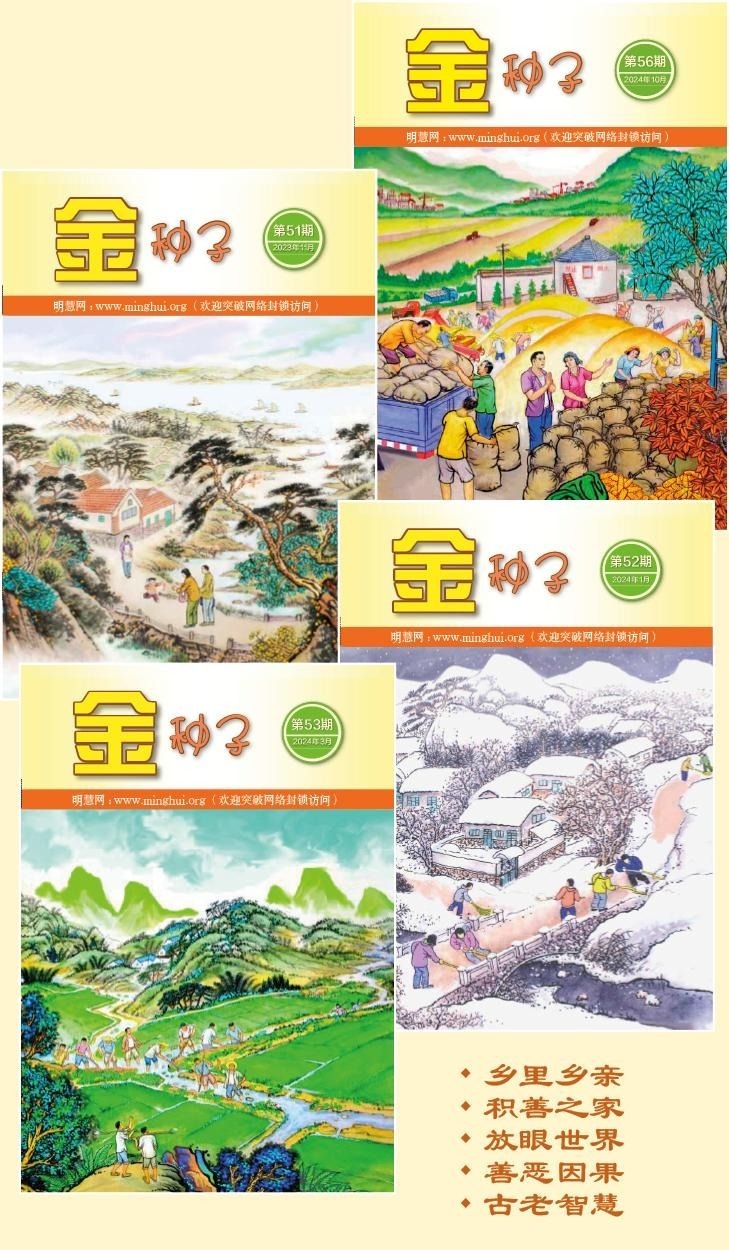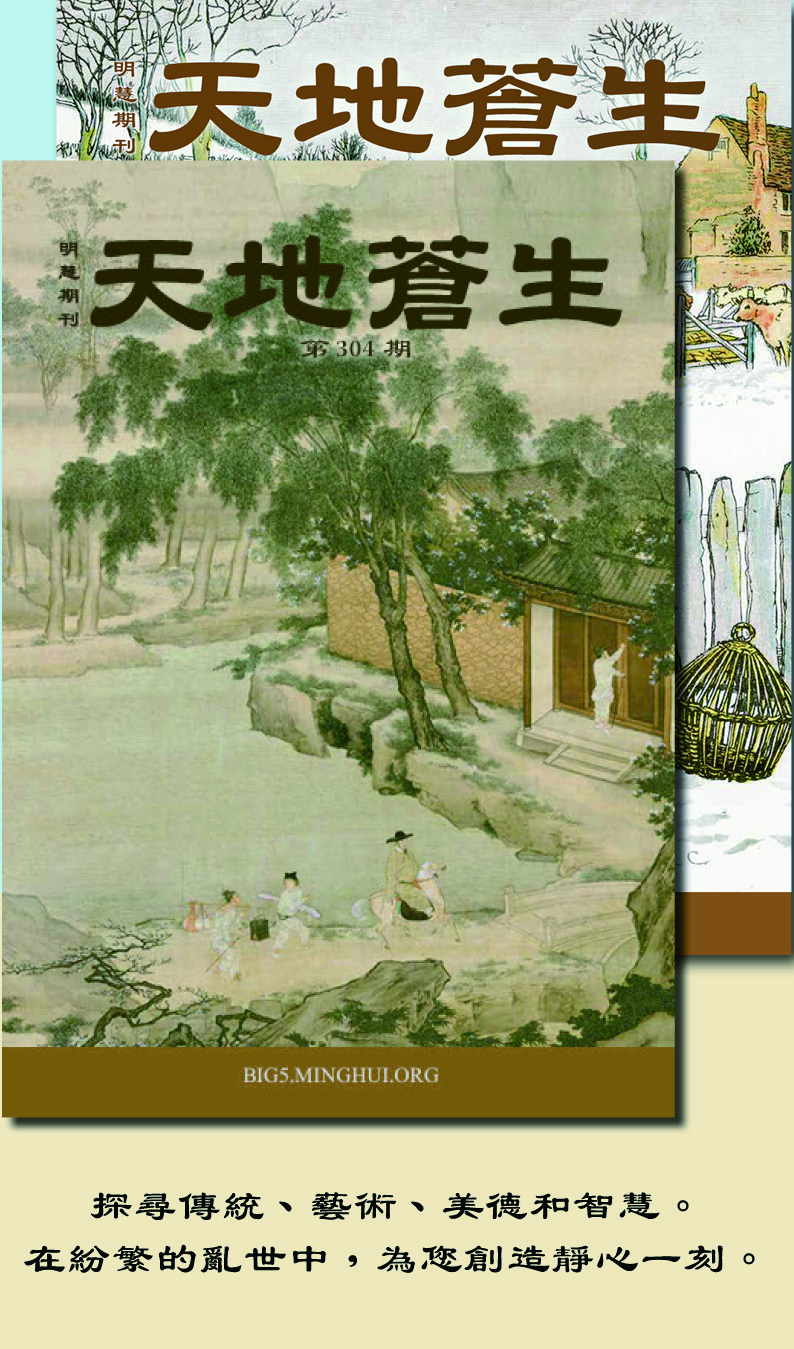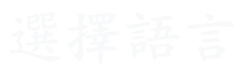放下人心 抓紧救度众生(译文)
尊敬的师父好!
同修们好!
我是二零一零年得法的学员。初次请到《转法轮》时,翻开书页便泪流满面,心中生出无限敬仰。此后无论是炼功、读经文,泪水总会自然涌出。这实在令人费解。正是这段经历,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功的决心。
初学功法时,恰逢家人六年前手术后的康复阶段。那段日子我日日挂念着他的身体状况,坚持带他接受治疗,直至他虽未完全康复却已无大碍。当确认他能正常生活时,我既感到安心又充满成就感,仿佛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。然而在这六年间,我的身体却日渐疲惫不堪。每晚八点过后,我便气喘吁吁地做家务,每年三月底总会持续数月的感冒。稍一外出,次日便卧床不起。朋友邀我喝茶,却因感冒久治不愈屡屡婉拒,想必他们觉得感冒拖这么久很反常,甚至因此让我得罪过朋友。我的妇科检查也显示患有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,我自身也感觉到身体的不适。虽未确诊具体病症,却深感全身无力。自开始学习法轮功后,这些症状骤然消失。最初我曾由衷感叹:若未遇见法轮功,自己或许早已不在人世。自接触法轮功后,我便放弃了原先信仰的宗教。
当时我对大法的认识尚处初级阶段,虽凭感性认知到法轮大法的神奇,但在如何始终保持大法弟子的正念,理性的认识大法上,我的经历很曲折,也曾有过违背法理的行为。起初我难以做到积极参与大法项目,因为内心存有“害怕被他人批评指责而受伤”的人心。这种状态难以突破。后听同修交流修去人心能消去大量业力的法理时,同修的话直抵我心灵深处,洗净了我的妄念,让我意识到自己竟用人心看待问题。后来有位同修开始主动帮我联系证实大法的工作。得法以来,我始终感恩那些牵引我、帮助我的同修们。
近一年来,在大法项目中我遇到了一些心性摩擦。开始时我质疑同修A的行为是否符合大法修炼者的标准——他行事不择手段,遇棘手情况便含糊其辞,强行推進项目,这种对大法不敬的态度令我难以容忍。我开始质疑A处理常人关系的方式,甚至主动为常人对A的批评充当中间人,对此我心里也很烦躁。团队内部也出现了批评声浪,当时我只看到A的缺点。一天我鼓起勇气,向A提出最困扰我的疑问:“你为何要发表对大法不敬的言论?”因为我认为我不问清楚这个问题,项目已经无法向前推進了。A回答说:“我从未说过那种不敬的话呀。”我回应道:“当时你的话令我震惊,所以我记忆犹新。不过既然你现在否认,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啊。”因为听了A的回答,我意识到她本人可能也已经认识到那些话本身不敬。我这才发现自己对她过于苛责了。后来与A交谈时,她突然脱口而出说:“C的慈悲心很强、从不责备他人。”这句话让我猛然惊觉,自己内心竟存在责备他人的念头。
某次交流会上,大家讨论如何对待A时,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向内找。我发现自己向内找时仍会将原因归咎于外人,存在指责他人的心态——这显然不符合修炼者的心态。然而在认识到自身不足后,过了一段时间,我又开始在意同修A的言行举止。
一次与其他同修交流时,同修发来信息说:“从修炼角度看,一切都是好事。看到自己的执著和不足,都是提升的机会。向内找,心存感激。”并附上师父的经文:“两方面都有问题,都抱着很强的人心。大法弟子合起来力量真的是非常大,发正念时大家都能思想集中,力量出来特别强,了不得的!烂鬼就是要干扰你们,就是要影响你们,让你们的人心发挥着作用,愤愤不平的,对谁看不顺眼,让你们人念强到你们的正念根本就使不出来!”(《各地讲法十四》〈大法洪传二十五周年纽约法会讲法〉)
看到同修传来的这段经文时,我意识到自己缺乏慈悲心。作为修炼者,指责他人、心生厌恶实非应有的态度,更违背了法理。无论他人优劣,都应向内找,修自己的人心。慈悲的对待周围的一切。此后,A的言行不再让我不平。我开始能看见她为众生奔走的付出,意识到她每日都在努力践行大法弟子的使命。我学会了感恩A点醒我的不足,并能与她协调工作。我深知A同样是师父珍视的弟子,正竭力精進修炼。
A在她母亲离世前的一个月里,一直持续给她母亲阅读《转法轮》。我反思到,此前我们合作项目时,面对常人与A的纠纷,在调解时我因顾虑而耗费过多时间,因而心生不快——若当时我怀有慈悲心,本不该感到不快的,本可对双方怀着温暖之心妥善处理。同时我意识到,自己还夹杂着图省事的安逸心,才产生了不快。未能真心实意为对方着想,这正是我作为修炼者的不足。如今才悟明白,常人把对A的投诉转达给我,实乃必然之事。
过去的我总想着既要守护自己的人心,又要为他人谋利。而师父教导我们的是做到真正的纯净、真正的无私。通过A的事件,我认识到不该因对方的言行去指责,而应怀有慈悲之心。
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讲真相的体会。
无论过去或现在(尤其过去更为频繁),我在炼功时常会看见多人面容交叠出现的景象。每当此时,我便意识到“必须向更多人讲清真相”,自此投身大法项目向众生传播真相。
我始终视身边相遇之人皆为有缘众生,外出时坚持分发大法资料。在家时,我也会向邮递员和快递员分发资料。在电车上遇到契机时,或是有人问路时,我都会递上神韵传单或干净世界卡片。
在此分享近期两个事例。其一是我曾向公寓楼内一位年长者B女士讲过真相。疫情前我向B女士介绍神韵演出,她当时表示理解。待疫情趋缓时,我忽然想到:“B女士应该还没去看神韵吧?”便决定登门拜访邀请她观赏演出。然而她的儿子出面婉拒说:“母亲患有认知症,外出极易引发躁动,无法前往。”B女士亦认不出我了,反问:“这个人是谁?”事后我深刻反省:若当初直接提出同行邀约该多好!救度众生的紧迫性由此刻入心间。
数日后,B女士竟将我家误认作她自己家,试图打开门锁。第二次发生同样情况时,我悟到“B女士是在寻求法”,当晚便前往她家询问:“要不要一起看神韵演出?”她儿子再次出面婉拒。
虽两度遭其子拒绝,我仍坚信定有办法。我重新审视:“身为大法弟子,唯有我能救度她。”“当今世间无人是普通人,背后皆有无数众生。”由此坚定正念与决心。下次相遇时,我决定请她念“法轮大法好”,观看神韵作品。
机会很快降临。数日后在公寓垃圾站,B女士突然从身后招呼我“早安”。我当即意识到“时机已到!”便去到她家中教她念“法轮大法好,真善忍好”,尽可能通俗地讲解真相,并让她观看了神韵作品。B女士表示理解。
后来再见B时,我给她看“法轮大法好,真善忍好”,但发现她已难以辨认文字。那次拜访实为告诉她真相的最后机会,我深切体会到:“救度众生刻不容缓,有缘相遇时必须当即讲真相。”
第二个案例是关于我的婆婆。去年三月,她被诊断出晚期大肠癌。六月初的某日,我梦见戴着白色口罩卧床垂危的婆婆却以明亮有力的声音与我交谈。梦中婆婆见到我时神情欣喜,用那熟悉的虚弱嗓音呼唤着我的名字。
当天恰巧接到丈夫通知,说婆婆病情急转直下。我立刻赶往病榻前,暗自下决心:“必须让她念‘法轮大法好,真善忍好’。”“除了我,再无人能救她。无论如何都要让她念。”我也向照顾婆婆的妹妹提出请她念“法轮大法好,真善忍好”,并给她发送了明慧网相关链接。妹妹自己开店,早前就常在店里放置神韵宣传单和海报,因此她立刻表示理解。
原以为跟婆婆还能长久相伴,正打算为她做些事情,如今却痛惜她临终将至。此时与婆婆相处的过往的一幕幕浮现出来,不禁感慨:“她真是个纯朴的人。”同时懊悔自己无能为力,我悲痛难抑。但转念想到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放下情,便重新振作起来。我始终提醒自己:必须以正念约束那份对死亡的悲恸与人间情愫。
婆婆非常顺从地诵念“法轮大法好,真善忍好”。连续三日诵念后,第四天她开始呼吸急促,第五日便离开了人世。此时我更深刻地认识到:“救度众生刻不容缓,缘分成熟时必须立即讲真相。”
自二零二一年父亲离世,二零二二年帮助大法活动的常人D先生(时年59岁)因癌症英年早逝以来,我对人世生死便逐渐萌生悲悯之情。D先生临终前,我去住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探望他时,建议他阅读《转法轮》,他欣然接受。读完一本书后,数周后他便离世了。D先生生前正义感很强,深受众人敬重。在他临终前去探望后,我食不下咽,同修见到我时也说我整个人透着忧郁。此后,连续三位帮助大法工作的常人离世,加上几位亲属相继辞世,每次都令我内心动摇。当时甚至连素未谋面的名人逝世都会让我心神不宁。于是,忧虑人类生老病死的心绪,以及与生俱来的寂寞之情开始显现。但渐渐意识到这或许是比常人更差的念头,才察觉到自己对人生中死亡观念的执著已层层堆积。我意识到,在面对各种事件时,自己的思考总被情感牵制,必须放下这些执著。
早前我便察觉到当我心态不端正时,寂寞之情便会浮现。后来在学习师父经文时我记起师父关于寂寞的一段讲法,自此,我发现自己已不再感到寂寞。对于逝者,我也能冷静的思考他们定能前往新宇宙。
得法十五年来,我深切感受到师父始终伴随我左右,在我悲悯,焦虑时,鼓励着我,始终守护着我。
师父说:“是你要在末后解体前签约要来世的,为救自己所代表的生命而修大法的。也就是说,你用生命来签约成为大法徒、要在大法中修炼的。”(《远离险恶》)
这句“你用生命来签约成为大法徒”(《远离险恶》)令我心头一震。我深切意识到:以生命为代价降临人世是肩负救度众生的重任的,这才是我真正需要铭记的使命。师父对我们的珍惜,远胜于我对自身的珍惜。作为大法弟子,我必须认清这份重大责任,恪守与师父的誓约。
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!
同修们,谢谢大家!
合十
(2025年日本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选登)
English Version: https://en.minghui.org/html/articles/2025/11/12/231283.html